
逃 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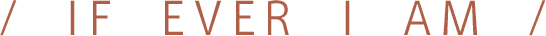

人生总是如此,
太多的东西,你越想珍惜,
它消失得越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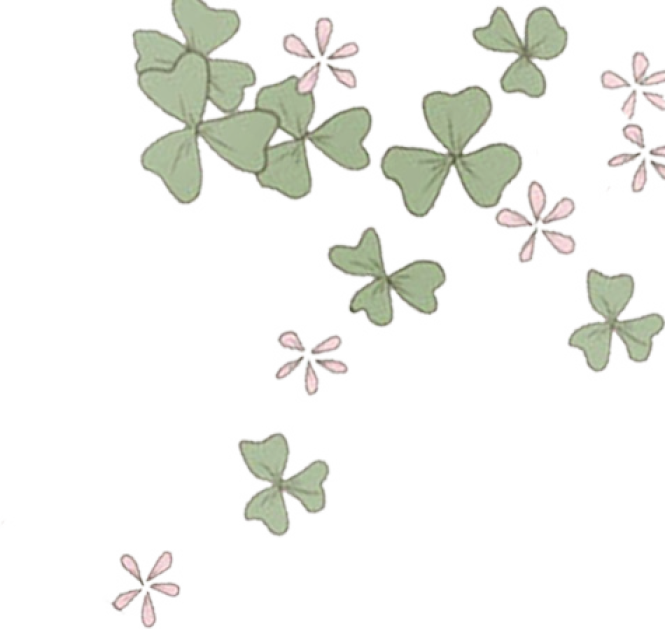
乔家轩去了楼下客卧,梳洗出来,遥控打开一整面客厅的窗帘。日月湖上白雾袅袅,恍若仙境。
他闭目深吸了口气,只觉得今天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甘甜。
这一觉,不知为何,傅佩嘉睡得极沉,哪怕乔家轩在身畔,她都没有半夜惊醒或者其他。
但醒来后,脑中依旧有些挥之不去的昏睡之感。傅佩嘉揉了揉额头正欲起身,下一秒,她看到了站在卧室窗前远眺风景的乔家轩。
他徐徐转过头,与她的视线碰了个正着。
不知是不是刚睡醒的缘故,他的目光深邃如无垠之宇宙。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他的话,不轻不重,但语气是命令式的。
傅佩嘉下楼的时候,白衬衫黑长裤的乔家轩围着围裙从开放式的厨房里转过身,手上端着两个盘子。
白瓷盘中,简简单单的一份早餐。是他亲手做的一份鸡蛋火腿起司三明治。他曾经说这是天下无双独一无二的乔氏三明治。
婚后的乔家轩但凡有不加班的休息日,最喜欢的便是带她出去走走,或者去郊外湖边野餐。他负责搭帐篷,提前准备好这种乔氏独一无二的三明治,她则负责水果和小蛋糕之类的。他钓鱼的时候,她便捧着一本书陪伴在侧,或是去帐篷小憩。两人经常早上出去,每每日落才返家。一直到后来她父亲生病,他工作渐多,才放弃这项休闲活动。
那时候的天空总是湛蓝无比,云如杂草,在两人的头顶聚聚散散,来来去去。
所以傅佩嘉吃过好多次,味道并不差。
事实上,乔家轩的厨艺十分好。从前,只要他肯下厨,她每回都吃得津津有味。
然此时,面对面坐着的两人,身边只余一室静默僵凝的空气。
傅佩嘉慢条斯理地吃着,完全食不知味。
乔家轩饮完了杯中的最后一口黑咖啡,取过沙发上的西装外套,转过头说了一句:“我去上班了。”
如从前一样的交代话语,令傅佩嘉握着热牛奶杯的手不觉一顿。
从餐厅的落地玻璃窗望去,可以看见他上车绝尘而去的画面。良久后,傅佩嘉缓缓地收回视线,取过白瓷盘,把上头几乎未动的三明治直接倒进了垃圾桶。
去了姜老头那里,又去了医院,再赶去咖啡店工作,等傅佩嘉回到了别墅的时候,已是半夜时分了。
室内灯光大亮,从落地玻璃窗望去,可见乔家轩认真办公的模样。他领结微松,袖子半卷,冷静睿智中有几分旁人瞧不见的慵懒颓废。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去楼上的书房,却在长长的餐桌上摊开了许多的文件。
不可讳言,这种回家有温暖灯光有人等候的感觉,对孤单寂寞彷徨无助了近两年的傅佩嘉而言,若说没有一丁点喜欢的话,那绝对是骗人的。
倘若这个人不是乔家轩的话,她想必是会更加欢喜。可又隐隐觉得,若那个人不是他,换作旁的人,哪怕是谭在城,傅佩嘉都无法想象。
这是一种非常幽微怪异的感觉。
傅佩嘉在冷风中呆立良久后,方缓慢地迈进了草坪小道。
听见她开锁进屋的动静,乔家轩抬起头。那个瞬间,傅佩嘉瞧见了一抹微光在他眼中划过,但随即便消失了,快得让人觉得只是灯光反射的错觉而已。
傅佩嘉垂头换鞋,不着痕迹地避开了他的视线。
如今的她,一有任何动静,便如刺猬般竖起尖锐的利刺,对他更是戒备不已。乔家轩是心知肚明的。他顿了顿,不急不缓地开口吩咐道:“我饿了。你把食物加热一下。”
仿佛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之事。
厨房的大理石台上有两份咖喱牛肉饭,白色瓷盘触手冰凉。
难不成他还没吃晚饭吗?傅佩嘉沉吟着把饭搁进微波炉里加热。忽然,她的视线一顿,看到了边上搁着的一束粉紫色的玫瑰。包扎精美,在灯光中蓬蓬盛开。
从前的那个人,在她生日或者纪念日的时候,偶尔也会带花回来送给她。因为次数极少,所以她每次收到都会觉得欣喜不已。
而如今,两人什么也不是。这束花显得特别突兀怪异。
数分钟后,“叮”一声,微波炉结束了运转。一时间,满屋子里充满了咖喱的香味。
这是傅佩嘉喜欢的菜色。平日里她工作兼职忙,来不及做饭,便会在星期六大采购,买一些蔬菜和牛肉,自己熬一锅咖喱。晚上下班或者夜里加班回来,饿了,便把冰箱里的咖喱浇一勺在冷饭上,放进微波炉里旋转两分钟。
每个饥肠辘辘的时刻,咖喱的美味胜过天下美食。
只是面对着的人是乔家轩的时候,傅佩嘉难免有些食不下咽。
乔家轩倒像是饿坏了,一勺一勺大口地吃着,很快便吃完了。
傅佩嘉早已经在咖啡店试吃过一些食物了,所以只吃了一半,便已觉得饱了。她搁下了勺子,准备收拾碗筷。
不料,乔家轩也不说话,伸手便取走了她面前的盘子。傅佩嘉眼睁睁地看着他低头就着她用过的银勺,三下两下地便帮她吃光了剩下的盘中餐。
开放式的厨房,长而宽大的餐桌,桌上的透明花器里插了几朵花边洋牡丹,簇簇拢拢堆堆叠叠地盛开着,满目韶华。
从乔家轩的位置,只要轻轻抬眼,便能看到不远处那个低头刷盘子的纤细身影。
很快地,傅佩嘉便刷好了盘子,又整理干净了厨房,便轻手轻脚地上楼而去。
她不在。客厅便似乎在一瞬间空旷清冷了下来,那种薄薄的寒凉一点点地围拢了过来,将他团团包裹。乔家轩试图让自己凝神静气,重新投入工作,但是他根本做不到。他整个人心里空洞洞的,心浮气躁不已。
乔家轩恨恨地一把推开文件,转身望着蜿蜒而上的楼梯台阶,胸口起伏不定。
卧室里,傅佩嘉站在窗边,头抵在玻璃上,默默地拽着透明的纱帘。窗外的日月湖黑洞洞一片,唯一可见的是湖对面住户的星火灯光。
听说一盏灯便是一个故事。但应该不会有与他们这样雷同的故事吧?!
离婚后的前夫前妻,没有一点爱地住在一起。
忽地,傅佩嘉察觉到了身后有人在靠近,正欲转头,乔家轩已经强势地把她固定在了落地玻璃窗与他之间,她完全无法动弹。
他抓住她的手臂,缓缓地吻在了她的耳畔。
傅佩嘉僵着身子推了推他,乔家轩似忽然恼了,他张口便恶狠狠地咬住了她的脖子。傅佩嘉吃痛,禁不住“啊”一声轻叫了出来。
也不知怎的,她的这一声呼痛令他瞬间又开心了似的,他松口发出了一声轻笑,但转头又咬了下去。
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咬得很轻,密密麻麻来来回回地在她脖子上啃噬。
第二天,可想而知脖颈处有一片啃噬齿印。但幸好,都没有上次在海岛时那么深,要足足一个月方才退去。
乔家轩已经去上班了。一楼餐厅,孤零零地摆着一份早餐,照例是牛奶和三明治。边上有一张银行卡和一张字条:我的工资卡,里面的钱用来支付家庭开销。
家庭开销这四个字却叫傅佩嘉怔然了许久。
她与他,一起住在这个屋子里,算是家吗?
自然不可能是。
关于两人之间,到底算什么,何时会结束,傅佩嘉亦不知。
说不定父亲过段时间就恢复了记忆。那么,两人之间也就结束了。
过一日算一日。虽然每一日都似在油锅里煎熬,但除此之外,傅佩嘉根本没有旁的半点法子。
数日之后,傅佩嘉便发现乔家轩连家政阿姨也没有请,除了早餐他负责外,屋子里所有的家务,洗衣打扫,买菜做饭,各种交费,她都必须亲力亲为。
至于姜家的工作,傅佩嘉起先是不肯辞的。
一来,经过这么多事情的她,发觉这个世界上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一个人还是靠自己最牢靠。二来,她喜欢在姜老头家的工作,在他和蔡伯两个人面前她可以很放松地做自己,她喜欢与他们相处。他们默默地尊重她关心她,投桃报李,所以她也用了十二分的心在工作上。
乔家轩听后,只扔下一句话:“你有两个选择,辞去工作或者结束我们之间的协议。”
这哪里是选择?傅佩嘉根本没的选。
她向姜老头和蔡伯辞职的那天,蔡伯愕然极了,迭声发问:“好好的为什么辞职?是不是嫌弃老头给你的薪水太低了?还是觉得太辛苦了?”
蔡伯都未待她开口解释,便急道:“傅小姐,你要是觉得薪水低,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这个蔡伯能做主,保证能让你满意。要是你觉得太辛苦,蔡伯就再找一个家政,分担一下你的工作。”
“没有。蔡伯,我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薪水少。”
“那是为什么?”蔡伯皱眉想了想,便“恍然大悟”了,“我知道了。肯定是那老头子又惹你生气了吧?你甭管他。他呀,就那张臭嘴惹人讨厌。其实啊,处久了你就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
傅佩嘉听了不由得微笑,她摇头说:“没有啦,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父亲醒过来了,我要照顾他,实在分身乏术,没办法继续再工作下去了。”
蔡伯听了这句话,便知道说再多挽留的话都没用了。
姜老头得知后,托着茶盏用茶碗盖拨了拨碧清的茶,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情。去吧。”
最后一天在姜老头那里的活,傅佩嘉干得认认真真,还写了一张明细单给蔡伯,什么物品放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段让老头子服什么药,以及老头子的各项喜好一一列了出来,十分清楚明了。傅佩嘉衷心希望接手的保姆可以尽快地进入工作状态。
“老头,我走啦。你要记得每天量血压,准时吃药。”
姜老头专注于山水画,头也未抬。
“老头,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傅佩嘉真心实意地道谢。
姜老头手里的画笔笔锋一顿,但他恍若未闻,什么话都没有。
傅佩嘉前脚才跨出姜家大门,蔡伯就从后面喊住了她,硬塞给了她一个厚厚的信封:“老头叫我给你的。他让我交代你,有空回来看看他。还有,万一在外面遇到了什么难处,就给我们打电话。
“记住了啊。有什么难处就给我和老头打电话。”蔡伯重复这一句话的时候加重了几分语气。
傅佩嘉走过那条幽深僻静的马路,转身的时候,蔡伯还站在门口目送她,见她转身,朝她挥了挥手。
傅佩嘉不是不感动的。
在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上,别人对你不好,是本分。对你好,那是情分。
傅家出事后,傅佩嘉经历许多人情变幻,所以蔡伯和姜老头给予的温暖,她倍觉珍贵。
只是很多的感谢她不知要如何表达,也唯有常记心间而已。
从咖啡店辞职那一天,傅佩嘉弹奏完毕,同事宛玲便含笑过来,指着角落里的谭在城对她说:“那位先生又来了。”
自打送出那朵玫瑰花后,谭在城只要在洛海,总是隔三岔五地过来小坐。一来二去,宛玲等同事也免不了打探。傅佩嘉实话告知,只是朋友而已。但宛玲等人却是怎么也不信。
每次谭在城一出现,她们便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傅佩嘉再解释也没用,也唯有随她们去了。
谭在城双手抱胸,一副若有所思的沉默表情。
傅佩嘉唤了他一声:“谭先生——”
谭在城陡然回神,定睛瞧见了傅佩嘉,面上才缓缓露出了一丝笑意:“傅小姐,你到休息时间了吗?”
这时,宛玲送了两杯咖啡和一些小点心过来,轻轻地搁在桌上,而后含意不明地微笑离开。
“谭先生,从明天开始我就辞职了。所以今天,请你一定要给我个机会请你喝杯咖啡。”
谭在城表情愕然:“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不是说在这里工作得很开心吗?”
这里头的曲折原委,根本无法对一个外人说清。傅佩嘉只好垂眼,苦笑不语。
谭在城忽然轻声道:“是因为你前夫,对不对?”
傅佩嘉愕然抬眸。谭在城他怎么可能知道乔家轩的存在?!
谭在城瞧出了她眼底的疑问,坦承不讳地道:“不错,我终于知道你是谁了。我也知道你的前夫是现今曾氏的乔家轩。”
“洛海城说大是大,但说小也小。场面上的人物也不过这些而已。会遇见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我和他交谈过几句。”
谭在城点到即止。他并没有告诉傅佩嘉,在昨晚的一个宴会上,乔家轩执着酒杯过来,道:“谭在城先生,是吧?”
眼前的人虽然很面熟,但谭在城确定自己是不认识他的。他沉吟不过一秒,对方已经自报家门了:“在下是乔家轩。我有一件事情想请谭先生帮个忙。”
原来此人便是洛海城中大名鼎鼎的乔家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谭在城欠了欠身:“不知乔先生要我帮什么忙?”
他们这个圈子里,想要刻意地认识结交某些人,向来的规矩都是通过交情不错的朋友代为引见的。朋友的朋友都是自己的朋友。如此一来,有什么商业上的合作也可以互为援引。绝少有这样子大大咧咧上前来做自我介绍的。除非不是同一个财富阶层的,找不到可以代为引见的朋友。但今日能拿到帖子出席城中段家宴会的人,身家背景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如此一来,那么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久经商场的谭在城明白这个理,所以客气礼貌中带有不小的防备。
乔家轩唇角微勾,单刀直入:“谭先生,请你离我的女人远点。”
谭在城皱着眉头道:“你的女人?不好意思,乔先生是不是弄错了?或者这中间有什么误会?”
“谭先生最近追求的那位——傅佩嘉,就是我的女人。谭先生是五福人,所以,想必不清楚我和她的关系吧?!”
骤然听到傅佩嘉的名字,谭在城呼吸停滞了一秒,好一会儿,他才不露声色地缓缓开口:“乔先生与她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愿闻其详。”
乔家轩浓密的眉梢轻轻一挑,答非所问:“看来谭先生很在乎她?”
“如果我说是的话,乔先生又准备如何呢?!”谭在城不甘示弱地回击,两人的目光在空中撞击出了微妙火花。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应该的。只是我的女人,谭先生还是离远点比较好。”乔家轩刻意地停顿了数秒,方吐出了后面的一句话,“这是我对谭先生的忠告!
“至于我和她的关系,估计整个洛海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谭先生想要知道的话,随便问一下场上的任何一个人即可。”
乔家轩是夺了妻家的财产而一举晋升洛海富豪圈的。他妻子的家族是鼎鼎大名的傅氏——傅氏?傅佩嘉?谭在城第一次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脑中似闪电般地划过一些事情,他似被大桶冰水浇头而下,整个人不由得一震。
乔家轩霸气地扔下这几句话便转身了。走了数步,他又站定了脚步,轻描淡写地道:“对了,听说谭先生最近在洛海,有块地正在审批中——化工方面,事关国家最关心的环保问题,政府最是慎重不过了。谭先生,你说是不是?”
谭在城不禁一凛。这个姓乔的果然是有备而来,绝对不可小觑。
当晚,谭在城便得知了傅佩嘉的真实身份,便是整个洛海城狗血故事的女主——傅氏千金,破产离异。他也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乔家轩面熟了,因为自己曾经在××岛,与乔家轩打过几个照面。
之前傅佩嘉给他的神秘不解之感,终于都一一解开了。
“佩嘉,无论你是谁,你过去怎么样,那些都已经过去了。”谭在城停顿了一秒,道,“上次说过,想请你去五福看看。现在春暖花开,五福莺飞草长,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间。”
如果自己拥有选择权的话,傅佩嘉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会考虑。
然而,如今的傅佩嘉实在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一团混乱和自己的不得已。
谭在城等了良久,可傅佩嘉一直紧抿着唇,从他的角度只看见她线条好看的眉毛和苍白清丽的脸。
原先他还是有过期待的,觉得乔家轩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很多男人都有类似的心态,属于自己的东西宁愿毁掉也不愿轻易让给别人。再说了,以乔家轩与傅佩嘉的关系,傅佩嘉怎么可能还与他有任何牵扯呢。
但此刻傅佩嘉的表情却叫他明白了过来,乔家轩说得半分不假。两人到今时今日依旧没有断干净。
“对不起,谭先生。”
谭在城虽然早料到了这个答案,但他总是不甘心。自打妻子去世后,傅佩嘉是唯一叫他动心的女子。遗憾离开前,谭在城问道:“佩嘉,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不是以最初的方式认识你接近你的话,你会不会就有可能接受我?”
傅佩嘉很认真地想了想,摇了摇头:“因为我一直重伤未愈,所以根本无法接受任何人。”
那么重的伤,想必这辈子都很难痊愈吧。
未承想,隔了不过两日,乔家轩居然改变主意同意她在咖啡店里继续工作,条件是:“只能白天工作,星期六星期天必须配合我休息。”
这家店又不是她开的,她能想什么时候上班就什么时候上班?再说了,咖啡店最忙碌的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这两个休息日以及每天夜晚时间。
不过,难得乔家轩同意,傅佩嘉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与咖啡店的经理丁瑛商量。
丁瑛听后,只说她考虑一下。
结果破天荒地,过了两天她居然答应了下来,同意傅佩嘉的工作时间调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工作半天,按时薪结算工资。
这样一来,每个月的收入自然是少了很多。但总算是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有个万一,自己好歹也还有份工作可以养活自己。
历经世事后,傅佩嘉懂得了凡事都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这一日,父亲傅成雄又问起了乔家轩。傅佩嘉便打电话征询袁靖仁:“明后天乔先生能安排一个小时到医院吗?”
袁靖仁:“乔太太,我查一下日程再回复你。”
求人办事矮一头,傅佩嘉这些天来,也只好对袁靖仁口中的“乔太太”这三个字妥协了。袁靖仁爱怎么唤她就随他去吧。
但等了好半天,袁靖仁也没有回复她。她再打电话追问,袁靖仁回她说:“乔太太,乔先生说知道了。”
这样是有时间呢,还是没时间?傅佩嘉一头雾水。
傅佩嘉并不知道,袁靖仁才汇报了她这句话,乔家轩冷厉如刀刃的目光便扫了过来。袁靖仁站在一旁等了好一会儿,乔家轩却只对他说了一句:“出去吧,我知道了。”
傅佩嘉当年在傅家,傅成雄疼得如珠如宝,不放心女儿开车,出入都有司机接送,所以傅佩嘉并没有学会驾驶。
搬入湖边的房子后,袁靖仁得过乔家轩的吩咐,曾转告过傅佩嘉:“乔太太,乔先生给你安排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如果你要用车,随时和我联系。”
但从搬入至今,傅佩嘉从来都没有用过车。她宁愿每日坐公交车辗转穿越整个洛海城去医院,去咖啡店工作。
乔家轩知道,傅佩嘉竭尽全力地想要避开他,与他划清所有可以划清的界限。
那天傍晚,傅佩嘉回到屋子,乔家轩已经在了,也不知谁惹了他,素来淡淡然的一张脸墨黑如炭。
他在生气!
如今的乔家轩,面对她的时候,是喜是怒,清晰可见。再无当年温温和和的那张假面具了。
也对。如今大权在握身家丰厚的乔家轩又何必遮掩自己的情绪,在她面前继续做戏呢?
现在的她,不配。
厨房的大理石台上,搁着他打包回来的数个食物盒,还有一束半开半合的杏色玫瑰。
也不知乔家轩是什么想法,每天下班都会带一束花回来。前日是黄色文心兰,昨日是粉色克罗威花。
傅佩嘉也不想招惹他,便默不作声地打开袋子,把饭菜一一倒进瓷碟中,放到微波炉里热一下。
不过片刻,就把他买来的三菜一汤都弄好了。
乔家轩依旧埋头在文件中,半点开动的意思也没有。傅佩嘉便去了楼上的洗衣房收衣服,准备折叠好了搁在衣柜里。
一堆的衣物,还在整理的时候,忽然只见乔家轩笔直地朝她走了过来,下一秒,他便劈头盖脸地吻了下来。
第二天,更衣室一地凌乱的衣服,傅佩嘉唯有重新再洗一遍。
只是乔家轩前一晚为何会生气,傅佩嘉半点也不知。而她也没有任何兴趣想去探知。
傅佩嘉起来得晚,下楼的时候,乔家轩已经准备好了早饭。他自己是培根煎蛋,而傅佩嘉的则是熬得稀烂的皮蛋瘦肉粥。
两人也不说话,就着餐厅明媚的阳光和餐桌上盈盈盛放的杏色玫瑰,吃完了早餐。
乔家轩端起咖啡杯,饮光了最后一口咖啡。沐浴在阳光下的傅佩嘉,头发随意扎成了一个丸子,露出白皙光洁的好看额头,蓬松慵懒。
她专注地喝着面前的粥,一直未抬头。
从前的从前,早餐的时候,她会不时地给他添咖啡,会抬头对他甜蜜微笑。那个时候,窗外洒进的阳光都不及她的笑容灿烂温暖。
可乔家轩知道,那样毫无保留地爱着他的傅佩嘉早已经消失了。
如果不是他,她还待在自己那个澄净明亮的水晶世界里头,单纯如白鸽。在那里,别人对她“微笑”,她也对别人微笑。别人对她“好”,她也对别人好。别人对她“真心”,她也对别人真心。在她的天地里,没有任何的心机设局,没有任何的利益纷争尔虞我诈。
记得有一次,林又琪心情不佳,半夜打了电话过来,她便想赶去安慰。
“又琪的爸妈吵架了,吵着要闹离婚。又琪很不开心——我想去陪陪她。”
他拦住了她:“都这么晚了,今晚就别跑这一趟了。乖乖地睡觉。明天一早我送你过去。”
“你不懂,如果不是特别难过,又琪是不会打这个电话的。如果易地而处的话,又琪肯定也会为我这样做的。
“她爸妈吵架这件事情是不值得我大半夜跑去他们家,但又琪她值得我这么做!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无比认真地对他说。
然而,傅氏破产后,她惶惶如丧家之犬,拖着箱子去了林又琪家,却被林家扫地出门了。
这一切,乔家轩都一清二楚。
林又琪父亲的小工厂素来与傅氏有合作,因有傅佩嘉这一层关系,林又琪在傅家出入自如,在傅成雄面前嘴甜地装巧卖乖,暗中不知给自己家带去了多少实质利益。
傅成雄出事,傅佩嘉对林家来说,自然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也只有傻傻的单纯的她,一直真心把林又琪当作自己的闺密,最好的朋友。
如果不是他乔家轩,她或许永远不会知道林又琪接近她是别有用心。
如果不是他,她就会嫁给黄品优或是类似门当户对的世家子弟,成为名媛贵妇,有傅氏在其身后为其撑腰,有傅成雄护她周全,有巨额财产在手,哪怕不识人心,一直纯真如婴孩,她也会安稳无忧地过完这一生。
事实上,他才是刽子手,亲手把她从云端推下,活生生地杀死了那个纯净美好不染半分尘埃的傅佩嘉。
思及此,乔家轩顿觉万剑穿心。
下一秒,他霍地起身,不发一言地离去。
片刻之后,傅佩嘉听见车子发动的声音,她缓缓地转头,只瞧见了车子绝尘远去的影子。
餐桌上的白瓷盘中,搁了他吃了一半的煎蛋。他分明没吃饱。
好好的一顿早餐,傅佩嘉隐约觉得乔家轩似乎生气了。
可他好端端的为什么又生气了呢?!傅佩嘉哪里弄得明白?
就像她弄不明白乔家轩在外面明明有别的女人,甚至不止一个,为何还会对自己这个前妻如此热情如火。每天下班都雷打不动地按时回来,好似这里真的是他的家一样。
除了陈小姐、谢怡外,她还看到过另外一个清纯白净的女生。
当时她从医院出来,在坐公交车辗转去咖啡店的路上,隔着公交车的玻璃窗,她看见乔家轩旁若无人地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臂,从一家很有名的甜品店里出来。他还体贴地为那女孩子开门,手里提着外卖的甜品盒子。
两人也不知说些什么,远远望去,只见乔家轩含笑的眉眼一片温润宠溺,神情轻松愉悦。
这样的乔家轩,是她从未认识的。
后来,公交车到了十字路口,一个转弯后,傅佩嘉便什么都看不见了。
陈小姐的自信大方,谢怡的妖娆妩媚,那个女生的娇俏可人,每个都自有风情。傅佩嘉虽不至于自惭形秽,却是费解不已的。
以乔家轩如今的身份地位,还纠缠她这个前妻做什么。
只是她从来不懂乔家轩。而如今,她更不可能弄懂了。
她的罩门落在乔家轩手里,无论他想怎么样,她受着就是了。
除了这样外,她又能如何呢!
两人住在一起后,对傅佩嘉来说,最欢喜的事情便是乔家轩出差。哪怕仅仅是两三天,她都觉得大松一口气,偷得数日一个人的清静时光。
这一日是星期六,傅佩嘉买了一大堆的材料,按度娘上的各种步骤,制作“佛跳墙”。她曾经答应过父亲的,只要他醒来,她就给他做他最爱的佛跳墙。
所需材料实在太多,她也只有精简了。至于钱方面,既然乔家轩给了她卡,她也就不矫情了,当用则用。
第一次取钱的时候,她看过里面的金额,并不多。第二次取钱的时候,存入的金额跟第一次所查询到的是一样的。看着样子,倒真有几分像工资卡。
足足忙了一个下午,把提前发好的鱼翅刺参等海物熬煮去腥,又把鸡鸭肚子蹄髈氽熟,最后把材料一一在罐底铺叠,倒入花雕,注入早已熬好的上汤,撒入少许调味料,盖上罐盖搁在灶上用细火熬煮。
她第一次做,海物又极腥臭,傅佩嘉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没忍住,趴在台盆上呕出了一些清水。但由于曾经对父亲有过承诺,她戴着口罩熬了下来。
一直忙碌到下午时分,她提着保温瓶去医院探望父亲。
“老爸,看我今天给你带什么好料来了?”
傅成雄用鼻子嗅了嗅,乐呵呵一笑:“闻着倒像是佛跳墙。”
“哇,老爸,你好牛!”傅佩嘉笑眯眯地打开盖子,盛了一碗出来,递到他面前,“你尝一口,味道怎么样?”
傅成雄尝了尝,问道:“在哪家买的?料是不错,不过也太偷工减料了,少了好几种料。”
“你猜猜。”
“福满轩?”
傅佩嘉摇头晃脑:“不是。”
“洛海会馆?”
“也不是。”
傅成雄又猜了一个,傅佩嘉依旧否定。
“整个洛海统共也不过三四个地方能做这道菜。你倒说说,到底是哪里买的?”
傅佩嘉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子,傲娇不已。
傅成雄嗤声笑了:“你做的?老爸才不信呢。你啊,撒谎也不打草稿。从小到大,你都没进过厨房,连棵青菜都烧不熟,哪里可能会做出这么复杂的菜式。”
老爸从来不知,有一年乔家轩生日,她立志要做一个入得厨房的女友,让乔家轩刮目相看,便暗中托林又琪的母亲帮忙找了一个四川厨师,学做川菜。
整整一个月,她天天和辣椒、花椒打交道。到了后来,都觉得自己成了爆炒的佐料,终于在切了N次手指,失败许多次后,成功地做出了一小桌的川菜。
这么傻的事情,这辈子,她只为他一个人做过。
然而,到了最后他还给她的,只是令她鲜血淋漓的几句话:“我从来都没有半点喜欢你……
“你忘记了吗?是你来到我家,脱了衣服,主动爬上我的床的。只要是个男人,谁抵挡得了这种诱惑。”
哪怕已过了这么久,但每次想起,傅佩嘉的心口都像是被人用刀片凌迟一般,痛不可抑。
“想蒙你老爸我,没门!虽然老爸最近病了一场,可精明着呢。你这丫头可骗不了我。”
傅佩嘉努力微笑,也不驳他。只要老爸喜欢就好,至于是买的还是她做的,根本不重要。再说了,万一他细究,她还必须说更多的谎来圆这个谎。
父亲吃完后,傅佩嘉拧了热毛巾,蹲下来给他擦手。她如往日般,用热毛巾托着父亲的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慢慢擦拭,细心温柔。
傅成雄忽然道:“佩嘉,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你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傅佩嘉顿时便酸红了眼眶。她垂下头,暗暗地吸了一口气把眼底的泪水逼了回去,方含笑抬头:“没有啦。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
傅成雄无言地摸了摸她的头发,扯开了话题:“你看,爸爸的头发有点长了,等下给爸爸理一下头发呗。”
“好。”傅佩嘉自然一口答应下来。
父亲卧床昏迷那段时间,她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方便,从某宝上买了一套简易的理发工具,试着给父亲剪头发。反正昏迷中的父亲没啥讲究,再加上男士的发型简单,一来二去,她也成了熟练工。
傅成雄照她的指示乖乖地在轮椅上入座,傅佩嘉用了洗发露给他干洗,轻柔地按摩头部。她边洗边调皮地问:“爸爸,舒不舒服?”
傅成雄缓缓闭上眼,说了一声:“舒服。”隔了数秒,他又说:“爸爸现在是不是一头的白发?”
“还好啦,只有几根而已。”傅佩嘉睁眼说着瞎话,哄着父亲高兴。
“傻孩子,爸爸老了呀,当然是满头白发,不用骗老爸。”
“爸爸不会老的。爸爸在我心里永远不会老。”
傅成雄又叫了她一声“傻孩子”,顿了好半天才又开口:“佩嘉,人总是会老的。爸爸也总有一天会离开你的。就像花开会花落一样,无须嗟叹。”
傅佩嘉心里头酸软一片,用手搂抱住了父亲的脖子:“不,爸爸,我不许你老。”
傅成雄缓缓抬手,拍了拍她:“傻孩子。”
“反正我不许你老。没有我的同意,老爸你就不许老,不许离开我,抛下我。”
“好,好,好。你不许爸爸老,爸爸就不老。你不许我离开你,我就不离开你。”傅成雄慈祥地微笑。
窗外的天空碧蓝如洗,云团清晰。
如此安详美好。
傅佩嘉真的想让时间停止它的脚步。
一辈子就这样与父亲待下去。
然而,人生总是如此,太多的东西,你越想珍惜,它消失得越快。比如时间。
给父亲理好了头发,又陪父亲说了会儿话,不知不觉,窗外日影静移,太阳已经到了落山时分。
回到与乔家轩两个人住的房子的时候,整个空间悄无声息。
看来乔家轩出差依旧未回来。她还是一个人。
空荡荡的屋子,空荡荡的大厅。佩嘉觉得放松的同时又有种说不出的幽微空虚之感。
在洗衣房收了衣物,又折叠好搁进衣帽间。忙忙碌碌了一天,她也有些饿了,便下楼准备炒个蛋炒饭随便果腹。
忽然,傅佩嘉在楼梯处停住了脚步。
客厅门口摆放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行李箱。傅佩嘉轻轻侧头,果然看到客厅落地玻璃窗前风尘仆仆的乔家轩。
下一秒,他结束了通话,转过身来,深深湛湛地望进了她的眼。
数日不见,乔家轩的眉目淡淡,瞧不出什么表情。
罐中剩下的那大半的佛跳墙自然全部落入了乔家轩的腹中。只是他也没说好吃或者不好吃。不过看他的脸色倒是不坏的。
那一晚,傅佩嘉洗澡出来,床头柜上照例已有一杯热牛奶在等候着她了。
傅佩嘉轻轻地触碰着杯沿,静了良久,方拿起杯子,缓缓地一饮而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