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 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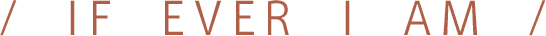

戒指的钻石在清亮的灯光下折射出炫目璀璨的冷冷光芒。
傅佩嘉瞧着瞧着,忽然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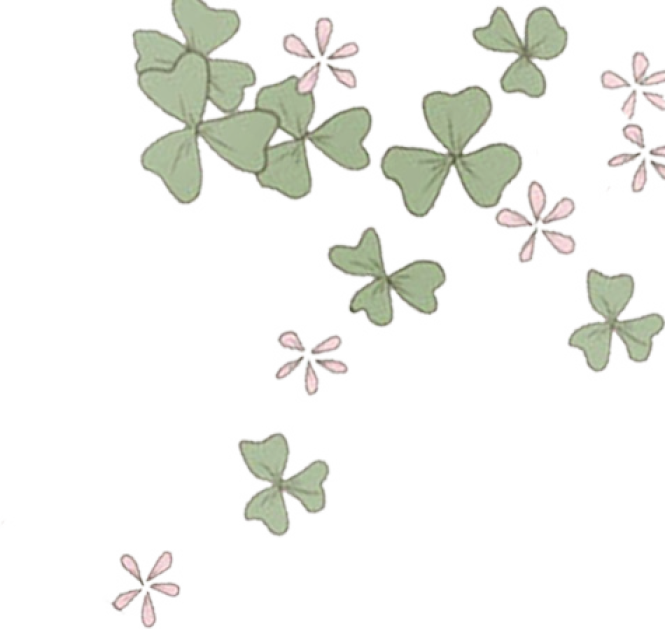
日暮时分,洛海城的半边天空似被人打翻了调色盘,泼下了变化万千的浓墨重彩。忙碌的街道,车辆蜿蜒如流水,潺潺不息。人声,车声,喇叭声,各种热闹喧哗声,交织成了一个众生繁华的世界。
夕阳的最后一抹微光悄无声息地探进了傅成雄病房的时候,傅佩嘉如往常般地推开了病房门:“爸,我来了。
“今天公司有点忙,要不是我对面的江伟帮忙,我这会儿还在加班呢……”
一屋子的寂静无声。
病床上已经昏迷了一年多的傅成雄自然不会回答她。
傅佩嘉自顾自地一边说话,一边利落地去洗手间拧了热毛巾,认真仔细地给父亲擦拭。
“老爸,你的指甲又该剪了。”擦手的时候,她这样说。
“爸,我给你翻个身哦。”傅佩嘉吃力地搬动父亲,给他侧了侧身,以防止产生褥疮。
病房里偶有电子监护仪发出的冰冷轻响,越发把整个空间衬托得静谧了起来。
如同这一年来的每一日,当她帮父亲做完最后的按摩理疗时,时针已经指向了六点二十分的方向。
傅佩嘉替父亲拉好了薄被,在他苍白枯槁的额头落下了轻轻一吻:“爸爸,我明天再来看你。”
这一切,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傅成雄是半点感知都无的。
或许这辈子,父亲再不会回应自己了。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父亲想必是怨她,所以才不愿意醒来看见她。
这一年多来,傅佩嘉总是自责不已。
经过护士台的时候,护士长林清唤住了她:“傅小姐。”
林清递了一份单子给她:“这是这个月的交费清单。本院所有的费用都是预交的。傅先生的账单是李长信医生帮忙打了招呼的。所以我们都提前用药了——”
傅佩嘉垂眼接过:“谢谢。我这几天会把钱交了。”
“好。傅小姐再见。”瞧着傅佩嘉远去的纤细单薄身形,林清不禁想起了数年前洛海城的那场名流云集、盛极一时的大婚。新娘所有的婚礼礼服皆出自国外某著名华裔设计师之手,连鲜花都是从国外空运至洛海。结婚当日,复古雍容的婚纱,如海的鲜花,却都美不过新娘流淌幸福的笑颜。
可眼前,当年的那个新娘眉目憔悴,早无当日半分顾盼神飞的影子了。
林清不免物伤其类,叹了口气:“女怕嫁错郎。咱们女人啊,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啊!”
新来不久的张雁容凑了过来:“傅小姐离婚了吗?”
一旁的邱敏冷哼了一声:“都这种情况了,两人能不离吗?那个乔家轩什么都得到了,自然要一脚把她踹了啊。前些日子报纸上都登了,傅氏都已经改名了。”
“唉,她前夫真是薄情寡义!”
林清:“你们都还没有男朋友,所以我这个老大姐啊,一定要叮嘱你们一句,日后找男友的时候可得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啊。这男人啊,脸好看是没用的,最重要的还是心地善良有责任感,要知冷知热懂得疼人……”
这些窃窃私语,傅佩嘉自然是听不到的。
又是一万多的交费清单。
薄薄的一张催款单,捏在她手里,却仿似有千斤重。
傅氏破产后,傅佩嘉便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家。父亲给她办理的所有附属卡自然都被银行停掉了。幸好,某张储蓄卡里有一小笔钱。以前的她,从未为钱费过半分心思,对金钱也没什么特别的概念。这笔钱是何时存下的,傅佩嘉自己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幸好有这笔钱,她方能借此度过人生最低谷的半年。
但如今的傅佩嘉早已经山穷水尽了。前些天,医院一连催了她两个星期,她都无法交上父亲的医疗费。李长信医生听说了她的情况,便用自己的名义担保,帮她申请了先用药后交费的特例。
想不到,到了最困难时刻,唯一会帮助自己的竟然是他的好友。
这真是个荒谬绝伦的世界。
傅佩嘉有的时候想想就觉得要发笑。但她根本无力扯动千斤重的嘴角。
这次的费用要怎么办?她手头所有的钱加起来不过四千多块而已。那还是一个星期前,公司发了工资才攒下来的。
从未尝过穷苦滋味的傅佩嘉,这一年来快被钱给逼疯了。如今的她也终于是知道了,从前在书上看到过的“一文钱逼死一个英雄好汉”的描写,绝非杜撰的。
此时,电梯“叮”的一声在某一层停了下来,傅佩嘉下意识地抬头。只一眼,她整个人便僵住了。
等候电梯的李长信医生大约也没有想到会遇到她,一时间也错愕未动。而他身畔那位身着定制西服,连领带都处理得一丝不苟的冷峻男子,则用目光徐徐地扫过了她,眼神漠然得仿佛只是看到了一件了无生趣的摆设物件而已。
傅佩嘉的下一个动作便是抬手按下了闭合键。两扇光亮如新的电梯门一分分地在眼前闭合,终于是关上了,将那个人隔绝在了外头。
像是躲过了一劫般,傅佩嘉从肺部深处缓缓地吁出了一口气。
可她还未来得及换气呼吸,电梯门居然又在她面前打开了。
电梯外,有只修长的手臂按住了电梯的打开键。下一秒,那手臂的主人已面无表情地跨了进来,在她前面站定。
那人不咸不淡地对着李长信道:“不进来?不是说要去开会?”
李长信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进了电梯后,他侧头与傅佩嘉打了个招呼:“傅小姐,你好。”
“李医生好。”傅佩嘉这样回他。
而后,李长信也不便再开口了。
静默的电梯里,连“嘎嘎”“嘎嘎”的钢缆转动声都清晰可闻。
傅佩嘉垂着眼,视线定格在自己破损的鞋尖。
这是一双国产××牌子的黑色尖头皮鞋,是傅佩嘉每日上班必备的。因为穿得多了,鞋头的皮早已经被踢掉了。傅佩嘉每月都捉襟见肘的,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再买一双。不得已之下,她便用黑色的马克笔把鞋头涂黑了,每天晚上用鞋油擦一遍,准备熬到过年,到了打折季再换。
如今的她,学会了精打细算,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来花。
想起以前拿着父亲附属的信用卡,一个下午可以花掉普通工薪族一个月或数个月工资的日子,傅佩嘉每每恍觉如梦。
数十秒后,电梯停在了下一层,进来了数人,将李长信和傅佩嘉三人推向了电梯的更深处。
两人之间几乎已无任何空隙了。傅佩嘉的后背已经紧贴在了电梯上,退无可退。四周都是那个人特有的强烈气息,她几近窒息。
会有人因为呼吸困难而在电梯里窒息而亡吗?傅佩嘉不知道。
不过,她却觉得这样也不错。
如果真能这样,她倒也解脱了。
片刻后,电梯再度停了下来,挤进了两个人。他往后顺势退了半步。傅佩嘉的额头因他的后退擦到了他挺括的西服外套。
那一秒,傅佩嘉如受电击,猛地将头往后一仰,只听“咚”一声,她的后脑勺由于动作过于猛烈迅速而撞到了电梯钢板。傅佩嘉因为疼痛而蹙眉闭眼。
可这疼,尚不及心口撕心裂肺的万分之一。
两人之间如此之近。她只要一伸手,就可以与往昔一样,搂住他精瘦的腰。
然而,傅佩嘉知道,此生再不会有那个光景了。
犹记得那一日清晨,她得知了傅氏的情况,惨白了一张脸问他:“钟叔叔说的可是真的?”
他居然毫无半点惭愧之意,沉静黝黑的眸子坦坦荡荡地望进她的眼,直认不讳:“是。钟秘书告诉你的,半字不假。”
她晃了晃,用尽力气牢牢地抓住了沙发的靠背,缓了许久才找到声音问他:“为什么?”
他张了张口,似有话要说,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她总是不甘心,想要知道原因。多可笑,被一个男人哄骗到这个地步,她却仍旧不肯相信。
他缄默地瞧了她许久,最后终于说话了。他的每个字都极低极缓,似在谆谆告诫她一般:“傅佩嘉,经过这一次教训,要记住了,下次不要再这么轻易地相信别人。不要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知道吗?”说罢,他转身打开了傅家两扇高大的门。
饶是到了那个光景,她却还存着一丝念想,她跑上前拼命地抱住了他:“家轩,我不信。我不信你会这么对我,这么对我爸爸。你告诉我,你是骗我的。好不好?”
背对着她的乔家轩一直没有说话。半晌后,他缓缓地扯开了她的手:“我没有骗你。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半分也没有。
“我与你在一起,我费尽心机地讨好你,哄你开心,让你爱上我,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包括‘我爱你’这三个字,都是有目的的。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傅氏。”
他每说一句,她便踉跄着退后一步……最后,她泪流满面地跌坐在了地板上。
整个世界仿若核爆,在傅佩嘉面前轰然炸裂成碎片。
此时此刻,乔家轩在她触手可及之处,所有的过往犹如倒带一般地不断闪过眼前。
傅佩嘉呼吸渐止。
就在傅佩嘉以为自己真的要窒息而死的那一秒,只听得“叮”一声,电梯终于到达了一层。拥挤的人如潮水般纷纷退了开去。
那人亦是,如那日一般,头也不回地跨步而出。
倒是李长信出了电梯,客气地转身对她说了一句:“傅小姐,再见。”
“再见。”除此之外,傅佩嘉实在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她没有因呼吸困难而窒息。
她还活着。
可眼前的一切都似盖了厚厚的玻璃罩子,什么都不真切。傅佩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坐上公交车,怎么下了车,怎么回到出租房的。
她回神后试图回想,但脑中完全空白一片。
唯一的意识是知道自己回家了。
虽然小,但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安全空间。傅佩嘉呆呆怔怔地坐在了老旧不堪的地板上,把头搁在床畔,无声无息地发起怔来。
花木兰悄悄地奔跑过来,竖着耳朵在她身边趴着。好久后,傅佩嘉才伸出手抱起它:“花木兰……我今天看见他了……”
从在傅家客厅摊牌的最后一面,到今天,已经是一年六个月零九天了。
傅佩嘉一直不懂。为什么深爱一个人,会换来这样子的结果?
孟太太的电话将她拉出了这一场伤心欲绝:“傅小姐,现在已经七点多了。你什么时候到?”
傅佩嘉这才慌乱回神,她居然错过了上班时间。她本应该从医院直接到孟家的。
“不好意思,孟太太,我马上就到。马上……”
“傅小姐,请你抓紧时间。和朋友们的牌局,我已经快迟到了。”孟太太的口气已不大和善了。
傅佩嘉忙把花木兰搁进了纸箱里,她进了浴室,洗了把脸让自己清醒了一下,便匆匆下了楼。
已经到点了,再坐公交车慢吞吞赶去的话,估计这饭碗就不保了。傅佩嘉不得已,只好忍痛打车去了孟家。
孟太太早已等得一脸不耐烦,见了她,十指纤纤地抓起包就往外走:“傅小姐,我丑话先说在前头。可别再有下次了。你都不知道,我的麻将搭子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过来了。”
“不好意思,孟太太。不会再有下次了。”傅佩嘉连声道歉。
孟太太养尊处优,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了午饭逛街做头发做美甲,晚上则雷打不动地与朋友们打麻将。看着孟太太,傅佩嘉经常会想到从前的那个自己。除了不打麻将外,同样无所事事,毫无精神寄托。
“没关系的,佩姐姐。我喜欢你,我不会让我妈妈开除你的。”孟家小公主孟欣儿跑过来拉住了她的袖子。
孟欣儿气鼓鼓地对着已关上的大门道:“妈妈天天就知道打麻将。我想她肯定把我生错了。她肯定宁愿生副麻将牌的。”
傅佩嘉被她逗笑了,蹲下来揉了揉她的头发:“欣儿,不许这么说你妈妈。这天底下,哪里有不爱自己女儿的妈妈呢。”
孟欣儿噘着嘴控诉道:“可是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更喜欢麻将。她要么不在家,在家也只会玩手机,从来不管我。”
“你妈妈也需要一点私人空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打麻将、逛街。再说了,她也会有事忙啊。”
“她才不会有事情忙呢。佩姐姐,要是你是我妈妈就好了。”
这话要是让孟太太听到,那还了得,她估计得直接打包走人。傅佩嘉忙正色道:“欣儿,不许乱说话。佩姐姐不喜欢乱说话的孩子。”
孟欣儿见她沉下脸,便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双手捂着嘴巴,眨着圆溜溜的大眼:“佩姐姐,我下次不会乱说了。你不要不喜欢我。”
如此可爱的表情,傅佩嘉怎么可能真生她的气呢。她蹲下来,摸了摸欣儿的头:“好。乖啦。来,我们先去做作业,然后温习明天要学的功课。”
偌大的公主房,粉色的墙纸,白色的家具,还专门为孩子开辟了一个摆放玩具的角落。
孟欣儿:“佩姐姐,我们今天语文考试了,我考了98分。老师说我这两个月进步很大哦。”
“欣儿好棒啊。来,让佩姐姐看看你错了几道题,错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下次要是再遇到同一道题目,争取不重复犯错……”
这是傅佩嘉的一份兼职。每晚的七点,傅佩嘉要到孟家,帮孟欣儿复习各门功课,照顾孟欣儿,给孟欣儿洗澡,哄她入睡,直到孟太太回来。
至于孟家先生,傅佩嘉兼职这三个月来,都没有看到过一回。
孟太太并不是个好相处的雇主。听孟欣儿说,在她来之前一年要换好多个阿姨。她已经是迄今为止做的时间最长的了。不过自傅佩嘉来兼职后,由于孟欣儿喜欢她,加上孟欣儿功课进步,孟太太对她也算和颜悦色,颇为客气。
这一年来,经历过了各种人情冷暖,也经历过了各种找工作,傅佩嘉对目前的这个保姆加家教的工作是很满意的。晚上兼职到深夜十二点,可以赚五千块,已经是极高的工资了。所以就算孟太太偶尔心情不好,对她发泄几句,她都默默承受。她白天在一个小公司任职文员,朝九晚五的,做足八个小时,也不过五千来块钱而已。
她早已经不是从前的傅佩嘉了,懂得了什么是形势比人强,懂得了什么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孟欣儿打开了书本,读了两页,忽然转过头,轻轻软软地开口:“佩姐姐,你今天怎么了?眼睛红红的。”
想不到欣儿这么细心,傅佩嘉心头微暖,便找了个理由想哄骗她:“今天晚上,佩姐姐做洋葱炒饭。切洋葱的时候,被它辣得流泪了。”
每到周末的时候,傅佩嘉会在自己租来的小屋做一顿简单的饭菜。洋葱炒蛋、西红柿炒蛋、咖喱牛肉等各种盖饭,好吃易做又省钱。
“切洋葱为什么会让人流泪啊?”孟欣儿懵懵懂懂。
“因为洋葱很辣,会刺激眼睛……”因为洋葱跟那个人一样,是没有心的,会叫人落泪。毫无预警地又想起了乔家轩,傅佩嘉忙一摇头,将他赶出了脑海:“好了。快订正试卷。还有一个半小时做作业。”
“佩姐姐,我什么时候可以念完所有的书啊?”做到一半,孟欣儿又歪头问她。
“最起码等你大学毕业。”
“等我大学毕业几岁?”
“怎么也要二十三四岁吧?”
“好讨厌,还要这么久!”孟欣儿颓然垂头,一脸的生无可恋。
傅佩嘉顿觉好气又好笑,努力做训斥状:“认真做作业。不许问那么多问题。”
孟太太照例又是深夜一点多回的家。她一进门便踹了十来寸的高跟鞋,从包里摸出两百块钱甩给了傅佩嘉:“辛苦你了,傅小姐。今晚打车回去吧。还有一百,算你的加班费。”
口气是愉快且施舍的。看来今晚她的手气应该不错。
两张粉红色的一百块钱轻飘飘地坠在了光洁闪亮的大理石地上。换了一年前的傅佩嘉,再多的钱,她也不会弯下腰去捡起来。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傅佩嘉不只捡起了钱,还客气地欠了欠身:“谢谢孟太太。欣儿的作业本你记得给她签字。”
“我知道了。”孟太太困倦地揉了揉脖子,见傅佩嘉没走,遂问道,“还有其他事情吗?”
傅佩嘉欲言又止了数秒:“我有件事情,想请傅太太帮一下忙。”
“什么事?”
“孟太太能不能提前给我结一下这个月的工资?”
“这个月你才做了二十天。”
“可否请孟太太帮一下忙?我……我急需用钱。”
孟太太沉吟了片刻,方道:“好吧。看在你平时做事勤恳的分儿上。我先把钱结给你。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
傅佩嘉拿着钱,千恩万谢地回了家。她甚至连羞耻都已经淡漠了。
天大地大,对她来说,真不如钱大。
东拼西凑,还是只有九千八百三十二块钱。
傅佩嘉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
医院的钱不够付,房租已经到期。房东这几天一早就在堵她。
这个月怕是连啃馒头和给花木兰买食粮的钱都没有了。
她喂花木兰吃了点自己晒的干草,揉着它松软的毛发,低低地道:“花木兰,怎么办呢?这个月的钱还是不够,我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够付医药费的工作呢?
“花木兰,我觉得好累……好累好累……”
傅佩嘉将头缓缓地埋在自己的膝盖处,极轻地道:“花木兰,我真怕我会熬不下去……”
花木兰自然不会回答她,它津津有味地啃着干草,吃得不亦乐乎。
无论如何,医院的钱一定要去交的,否则医院要停掉治疗了。下个月的房租就“请”房东再宽限几日吧。
第二天一早,刚结束会诊的李长信已经接到了相关的内线电话:“李医生,你关照过的那位傅先生,上个月费用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没有交上来,这个月我们部门是否要继续治疗?”
那头颇有几分为难,一再解释道:“李医生,我们医院的相关规定你是最了解的。”
李长信扶了扶眼镜,道:“继续吧。”
“那下一个月的相关治疗费用呢?”
“先以我的名义欠一下。这样会不会让你们难做?如果需要什么申请担保的话,你这边安排一下,到时候我过去签个字。”
“好。那请李医生在方便的时候来我们科室签个字。”李长信是叶氏医院院长的女婿,医院日后的接班人之一,各大科室谁敢不给他这个面子?!
“好的。麻烦你了,姬主任。”
结束通话后,李长信沉吟了数秒,从外套口袋里摸出手机打出了一个电话。那边嘟了几声方才接了起来。
“在忙?”
“在开会。”
“那我不打扰你了。”
“我让他们都出去了。怎么了?傅成雄的病情出现新的情况了?”乔家轩捏了捏发涨的眉心,漫不经心地问道。
“我找你是因为傅小姐。”
那边突地沉默了下来。
“上个月的治疗费用,她到现在还没有交。”
电话那头依旧无声无息,似那人已经凭空消失了一般。
“看来她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恭喜你了,乔。良愿终成。”李长信不咸不淡地说完这句话,也不待乔家轩回答,便挂断了电话。
乔家轩盯着自己掌中的手机,他不知道自己这样的姿势维持了多久。直到助理袁靖仁敲门进来:“乔先生,已经休息半个小时了。要继续会议吗?”
乔家轩反手把手机盖在了会议桌上,再抬头时,面上已经平静从容,毫无方才通话时的半丝波澜了:“让他们都进来吧。”
袁靖仁转身而出,手刚握到门把,忽然听见乔家轩的声音响起:“今天是几号?”
袁靖仁回道:“6号。”
乔家轩似想起了什么,脸上的失神一闪而过。
众人进来继续方才关于投资案的讨论。身为助理的袁靖仁明显地察觉到了乔家轩的心不在焉。
“乔先生,按目前评估,孤儿院这块地改建投资案的可行性大,获利高。如果董事会通过的话,我们可以立刻着手进行收回孤儿院土地的事项……”
乔家轩靠坐在办公椅上,修长的手指抵在下颌处,若有所思,良久不语。
“乔先生……”
乔家轩不带情绪地抬了眼,扫了一眼这个提案的彭经理,沉吟道:“关于孤儿院改建的这个方案,我们下次会议再做决定。下一个讨论项目是什么?”
他的声音淡然,却带了不容置喙的威严,在座众人听在耳中,便已经知道他对这个提案并不满意。
这个方案本是在乔家轩指示下进行的,彭经理所在的部门一个多月来加班加点地进行各种资料收集和评估工作,本以为今日会议可得到乔家轩的另眼相待。但怎么也没料到,乔家轩十分不耐烦,语气里头隐隐有否决的意味。
商场如战场,公司内部部门之间又何尝不是战场呢。若是这个方案不通过,今年部门的绩效怕是……彭经理诚惶诚恐地坐着,一再回想自己的表现,实在不知自己方才的简报到底哪里错误了,会让乔家轩如此不满。
下午又是冗长的会议,一直持续到了五点。乔家轩看了腕表,对众人吩咐道:“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再继续。”
出了会议室的乔家轩径直进了电梯,按下了去地下停车场的键。
乔家轩把车子停在了医院的门口。十几分钟后,只见一身素简的傅佩嘉从公交车上下来。不同的是,今天的她提了一个小纸袋,走进了大楼。
乔家轩一动不动地坐在驾驶座上,望着傅佩嘉的身影一点点地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尽头。
恒温的病房内,傅佩嘉照例给父亲翻身,给他的四肢做按摩,以防止长褥疮和肌肉萎缩。
一切结束后,她取出了纸袋里的纸杯蛋糕。这么小小的一个,要十五块钱。平时,这个开销够她买四天的早餐了。
不过今天是自己的生日,难得地破费一下。
虽然一再地告诉自己别再回忆从前了,可有些时候,傅佩嘉总是不免会想起,每年这个时候,她起码要过几天的生日,切好十个八个蛋糕,许好多好多个愿望。
听说人一辈子的福分是定量的,若是自己不懂珍惜,过度挥霍的话,便会很快地把一辈子的福气用光。
傅佩嘉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
在她人生的前二十多年里,她属于被上帝宠幸着长大的为数不多的一拨人。富二代,含着金汤匙出生,白富美,有财又有貌,所有形容家世容貌的美好字眼都可以用在她身上。
或许是因为过往的她不懂得感恩惜福吧,所以今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给自己唱生日快乐歌。
傅佩嘉双手合十许愿,吹灭了那根从蛋糕店特地讨来的蜡烛。
“老爸,今天我又大一岁啦。
“我现在啊,不仅学会了洗衣服打扫,还学会了烧菜做饭。我烧的番茄炒蛋、洋葱炒蛋还不错哦。萝卜排骨汤、海带排骨汤,各种排骨汤几乎都难不倒我哦。厉害吧?!老爸,你快醒来吧,醒来我就做给你吃。我保证你会喜欢。
“不过你最喜欢的佛跳墙我可不会,材料太多太贵,而且很耗时间——不过这样吧,我答应你,只要你醒来,我一定去学做这道菜,做给你吃。好不好?
“老爸——你醒过来吧——
“我好想好想你啊——”
可病房里唯一会回答她的依旧只是监护仪上冰冷的“嘀嘀”声响而已。
傅佩嘉仰头吸气,极力控制不让眼眶里的泪掉落下来。这一抬头便扫到了时钟,此时已经是六点半了。傅佩嘉忙起身把蛋糕装进了袋子,又匆匆替父亲掖好了薄被:“老爸,我要去上班了。明天我再来看你。”
“傅小姐,这个要给你。”林清在走廊上截住了她,默默地把催款单递给了她。
“我会尽快交费的。”傅佩嘉垂眼说着每个月重复的话语。
“好的。傅小姐,那我先去忙了。”林清点点头,便急匆匆地走开了。她知道傅佩嘉的情况,怕她尴尬。
饶是如此,傅佩嘉也依然觉得难堪至极。
她明白他们不催促是因为知道她已经山穷水尽了。
公交车上乘客很多,人群一拨拨地拥上来,又一拨拨地退去,傅佩嘉被挤到了最角落。车窗外,是熙熙攘攘的车流。
偶尔的偶尔,傅佩嘉站在马路边,会对着那些飞驰而过的车子发愣。她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自己扑上去,“砰”的一声响起,是不是一切就可以结束了?!
幸好,这样的念头每每只是一闪而过而已。她回神的时候,都忍不住打冷战。她告诉自己,还不能死。父亲还活生生地躺在医院,没有醒来跟她说一句“我原谅你”,她就不能死。
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早已经精疲力竭了。
“刺”一声长刹车声传来,公交车到了孟家这一站。傅佩嘉已饥肠辘辘。她看了看手机显示的时间,还剩十分钟。也就是说,她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填饱自己的肚子。
于是,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傅佩嘉站在垃圾桶边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今天的生日晚餐——一块面包和那个纸杯小蛋糕。
而马路边,一辆一直尾随着她的豪华车子里头,乔家轩缄默无声地将这一切都瞧进了眼中。
孟太太照例出去会牌友了。傅佩嘉给孟欣儿辅导功课的时候,门铃声响了起来。
门口站了一个长相普通的中年男子,大约是喝了不少酒的缘故,眼神迷迷瞪瞪。他见了傅佩嘉,似也惊了惊,踉跄着往后退了两步,再度确认了一下门牌,方粗声粗气地问道:“喂,你是谁?怎么会在这里?”
“请问你找谁?”浓烈的酒气扑鼻,傅佩嘉不由得皱眉。
“找谁?”那男人斜着眼瞧她,奇奇怪怪地笑了。他推开傅佩嘉,一边跨了进来,一边大声喊道:“欣儿,欣儿——爸爸来了,还不快出来。”
孟欣儿听见声音,从自己的房中跑了出来,大喊了一声“爸爸”,便飞扑进了男子的怀抱:“臭爸爸,坏爸爸。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来看我?”
傅佩嘉吃惊地呆立一旁,这才意识到此人居然是孟先生。
“你妈呢?不会又去打麻将了吧?”
“没有。妈妈她出去给我买东西了。”欣儿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打麻将,小小年纪已经懂得为母亲遮掩了。她偷偷地对傅佩嘉眨了眨眼,示意傅佩嘉“快叫我妈妈回来”。
傅佩嘉立刻接收到了信息,她转身发了一条信息给孟太太。
“她是谁?”孟先生问自己的女儿。
“佩姐姐是我的保姆家教,帮我辅导功课。佩姐姐教得特别棒,老师说我的语文和数学进步很大哦。爸爸你来看,这是我新考的语文卷子,我考了一百分哦。”孟欣儿蹦蹦跳跳地拉着父亲的手进了自己卧室,像极了一只快乐的小鸟。
“我们欣儿太棒了。让爸爸想想奖励你什么好呢。”
难得欣儿这么喜欢一个保姆。看来这保姆不简单啊。孟先生眯着眼,仔细地打量了傅佩嘉一番。
那一晚,由于孟先生的到来,傅佩嘉提前回了家。
习惯了晚归晚睡,难得早回家,一时间竟有些无所适从。傅佩嘉取出了钱,又翻来覆去地点了几遍。今天因为买了纸杯蛋糕,买了面包,又少了一点。
怎么办?全部交给医院,还是不够。她该怎么办呢?
她茫茫然地呆坐在床畔。
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件物品突然划过了脑海。傅佩嘉腾地站了起来,在老旧的小柜里翻找了起来。
一件粉色粗呢外套的出现,令她的眼睛一亮:对。就是这件外套。
没有。还是没有。
终于,在摸到最后一个口袋的时候,她的手指碰触到了一个冰凉的金属物体。
傅佩嘉小心翼翼地摸了出来。
戒指的钻石在清亮的灯光下折射出炫目璀璨的冷冷光芒。
傅佩嘉瞧着瞧着,忽然笑了,只是这个笑容比哭还难看几分。
这是她和乔家轩的婚戒。
当日浑浑噩噩地离开,忘记了手上的这枚戒指。如今倒是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